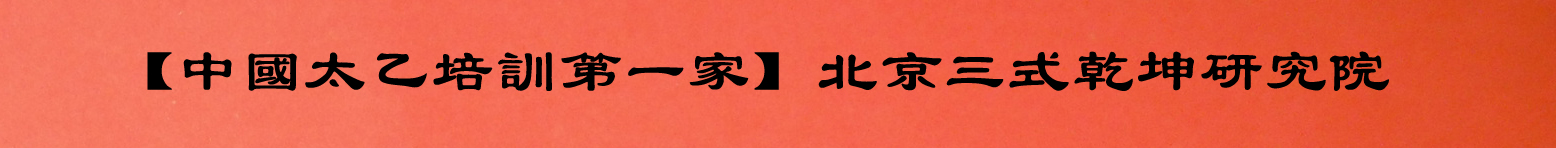易学动态
重读《古法论命纲要》有感
——兼论命理“复古”主义
初读陆致极先生《古法论命纲要》是去年的事。该书梳理了“古法”的发展脉络,还原了“古法”论命模型及推演方法,逐一介绍了与“古法”相关的经典,并对“古法”的历史地位做出了公允的评价。
今年命学界“复古”声浪又起,甚至有人断言命理学未来10年必定是“复古”的世界。于是,我又重读《古法论命纲要》,对“古法”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下面谈点个人看法,供同好参考。
一、《古法论命纲要》是研究古法的典范
如何对待命理古法,确实是值得重视的问题。但不管立场如何,首先得有一个科学研究的态度,不能因为喜欢就说它完美无瑕,也不能因为憎恶就说它一无是处。中国学界尤其在传统文化领域,常耽于立场先行,甚至拉帮结派,搞门派斗争。这些都是问学之人所不齿的。
熟悉陆致极先生的人都知道,他原本研究语言学,有多本著作传世,却因早年与命理学结下的奇缘而转为从事命理研究,并将命理学现代化、科学化、学术化作为一生志业。为什么倡导现代化的人要去研究“古法”呢?
(一)《古法论命纲要》是关于命理古籍的知识考古学
陆先生在《古法论命纲要》自序中坦言:
十年前写作《命运的求索》的时候,对古法经典只是做了浏览和提取要义……这次,真是下了决心,叩门走进橱窗,跟这些模特儿(指古法)面对面的对话,了解她们穿戴的这些服饰的设计思路、特征以及它背后要表达的没学理念。
这是典型的知识考古学独白。有社会科学研究背景的人都知道,知识考古学的核心是通过梳理话语的历史形成过程,揭示知识(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)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,而非将知识视为客观、永恒的真理。它不关注知识的“正确性”或“进步性”,而是聚焦知识背后的权力机制、话语规则和历史条件 —— 即某一时期的知识为何以特定形式出现,哪些话语被认可为“真理”,哪些被排斥为“异端”,这些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社会、政治或文化逻辑。
陆先生的《古法论命纲要》正是秉持这种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态度,对“古法”经典进行了一系列的知识考古。在该书中,他从六十甲子纳音谈起,参考睡虎地秦简、银雀山汉简所涉内容,考证六十甲子纳音的起源,并通过对敦煌写本甲乙两种释文的比较,对六十甲子纳音进行了深度解读。在此基础上,陆先生从《李虚中命书》讲起,对《玉照定真经》《珞琭子三命消息赋》《巫咸经》《五行精纪》《三命指谜赋》《应天歌》《兰台妙选》等“古法”经典进行了逐一释读,并从这些经典中复原了“古法”的论命模型和推理方法。他特别指出,“古法”或者说李虚中三命法的论命框架,就是三元四柱,推理的基本工具为纳音五行。在此基础上,他又从“三元九限”出发,对“古法”如何推算本运、大运、小运做了归纳。最后,通过梳理古法与今法的交叉发展,回顾了古法逐渐“隐退”、今法最终取代古法的简要历程,重点分析了这一变化的历史原因。
在陆先生看来,“今法”对“古法”的替代完全是一种范式对另一种范式的替代,并从思想史的角度,分析了两种不同范式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。他指出,古法“以年为主”的论命范式,恰好反映了当时社会盛行门阀制度的社会现实。今法“以日为主”的论命范式则出现在门阀制度逐渐消退之后的宋朝时期,正是个人因素在科举时代的重要性,才使得论命主体从以年为主转变为以日为主,这自然也是当时社会历史变迁的反映。
现在有一种看法,认为李虚中所处的时代已然实行了科举考试,但为什么他所创立的“三命术”依然“以年为主”呢?产生这种误解可能有两个原因:
一是对门阀制度的发展历史了解不够透彻。尽管隋朝即已开始科举取士,但门阀制度在有唐一代依然盛行,直到宋朝建立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所以,李虚中受门阀制度的潜在影响势所必然。
二是对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规律认识不足,缺乏基本常识。学术思想史是后人对前人学术成果的归纳总结。任何学术思想都有其时代背景,也必然受到所处社会历史的深刻影响。但这种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,身处其中的学者或者思想者往往感受不到它的存在。比如说我们命理学的祖师爷在创立“以年为主”论命框架时,可能根本就没意识到门阀制度在思想上对他们的影响,但门阀制度对他们的所思所想必定是有深刻影响的。
为什么会产生“以年为主”的论命架构及其理论呢?这背后固然与理论提出者个体有关。作为一种思想,它的产生固然要受个体的影响,不同个体有不同的思想。但思想所处时代的影响,必定大于个体差异产生的影响。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,后人在做思想史研究时,往往更加注重发掘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。
为了让读者更清楚理解这个道理,我们把话说得更直白一些。认定“以年为主”的论命思想受门阀制度影响,这是后世学人研究得出的结论,而不是先师们事先体悟到门阀制度对他们的影响(当时也没“门阀制度”这个术语)。但是,不能因为先师们没有体悟到门阀制度对他们的影响,就说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门阀制度的影响,就跟我们本身没有见到磁力线就否定磁场对我们的影响一样。论命主体的变化实质是学术思想的变化,而思想的变化必然与时代变迁有关。这在思想史上就是基本常识,不是靠谩骂就能否定得了的。
(二)“古法”研究的难点何在
现在,命理学界出现了一股以“复古”为口号的小群体,颇以主流自居。但不得不说的是,研究“古法”是有门槛的。实事求是地说,不是那些以“江湖派”自居者能懂得的。难点何在?一是现存“古法”典籍数量有限且版本不一,且金沙杂陈,难以辨别。二是现存古法典籍大多文字古奥,难以理解。这里面,既有文字的原因,也有基础知识的原因。文字的原因得多说两句,命理之学在民间过去多以口口相传为主,极少有文字流传。还有就是有些命理师为了保密,故意将文字藏头去尾,写得晦涩难懂。加上命理中用到的知识多数脱胎于天文历算,没有这方面知识是读不懂的。三是古法典籍中缺少具体案例,社会上也未见古法命书实物。有这些“致命伤”,后人就难确切知道古法论命的完整体系了。至于今日那些依靠“今法”排盘软件摆弄出来的所谓“古法”论命,也就哄哄小孩而已。据说那些标榜“古法”论命者颇有市场,常出入达官贵人之所(据其徒众讲),可谓春风得意马蹄急。我就纳闷了,那些达官贵人应该是有一定文化的,可他们为何就那么容易被“古法”大师们唬住呢?其实,韩非子早就说过:画鬼易,画犬马最难。犬马谁都见过,画的像不像,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至于画鬼,因为谁也没见过,他说是,咱也没法反驳。同样的道理,典籍里没有具体例子,市面上又没有古法论命的留存物,他用今法的APP排盘却硬说就是古法论命框架,有识之士难道还会去跟这种咬定“三七二十三”的人争辩吗?
陆致极先生正是出于让更多的人真正了解“古法”,从可见的“古法”原典入手开展研究,形成了这一划时代的“古法”研究成果。
这对于中国命理学界无疑是一种福音。但是,个别号称独得“古法”秘技者却以“书房派”呼之,以“书生论命”损之,这又居心何在呢?本来学术争鸣嘛,你有不同看法,写书发文章辩难就是,何以要进行人身攻击呢?无他,陆先生的最新研究成果戳破了他们的画皮,让学界同仁和广大的命理爱好者看到了真实的“古法”!你根据原典复原了古法论命的真实架构,坦言具体的操作流程,这让我再到哪里去扮“神仙”蒙人呢?对于这样的人,翻脸大怒是不足为怪的。
二、《古法论命纲要》的学术价值
一提到学术价值,可能又要被某些人讥为“书房派”了。如果有人这样称呼我,我倒是非常乐意接受。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,从李虚中到万民英,从沈孝瞻到徐乐吾,这些命理大家无一不是妥妥的“书房派”。能与这些祖师级的“书房派”同列自然是求之不得,只是小可自知无此德行与能力罢了。我们今天能有古籍可供研究(包括今法),不都得感谢当年的“书房派”吗?陆先生的研究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学术价值:
(一)首次复原古法论命体系
该书通过对古法经典文献的解读,展现了古法的发展脉络,从《李虚中命书》《玉照定真经》《兰台妙选》等典籍中复原了古法论命的模型——“三元四柱”,并对以纳音为工具的推演技法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(比如要关注轻重、盛衰等)作出了阐述,指出仅看干支特殊组合论命的不足,客观评价了古法及其典籍的价值。
(二)倡导了一种科学化的学风
该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复原“古法”样貌,更在于通过结合历史语境的剖析示例,展现了一种科学化、规范化的学风。陆先生曾在多本书中袒露了将命理学领入学术殿堂的初心,所以他始终坚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。他研究古法,也是老老实实从文本研究入手,分析文本的本来意义和传承关系,并未借此自高身价或者宣称什么发现。这无疑给后学者树立了命理学研究的榜样。当然,那些打着“复古”旗号的人或许并不在乎什么学风。他们惯用的伎俩就是故作高深,打出玄之又玄的招牌,说些神秘兮兮的江湖话术,蒙骗无知。
(三)揭示了古法到今法的演进逻辑
陆先生通过对《李虚中命书》《五行精纪》等古法典籍的梳理和解读,揭示了从“以年为主”和以纳音为主的古法转变到徐子平确立的“以日为主”“ 专主五行” 的过程,用事实证明今法并非彻底否定古法,而是在继承干支五行框架下,通过方法论重构实现论命范式的革新。这个过程的演进理路,就是从经验总结到逻辑推演,从服务贵族到服务大众,从神秘主义到理性化分析,揭示了从古法范式向今法范式发展的必然规律。
陆先生特别指出,在古法“隐退”之前,万民英等大家曾竭力为其“生存”作过最后努力,提出“以五行为经,参之以纳音为纬”的解决思路。但“古法”最终并没有如万民英所愿,它在明朝中叶以后还是从主流命坛上“隐退”了。值得注意的是,陆先生在《古法论命纲要》中,只讲“古法时代的终结”,并未讲“古法论命的终结”。这样的表述,与他“研古而不复古”的主张是高度契合的,也是始终如一的。
陆先生还在一篇文章中用科学“范式”的嬗变原理,对“今法”取代“古法”作出了学理上的分析。有兴趣者不妨找来一读。
三、对“复古”主义的思考
当前,命理学界有人主张理直气壮的“复古”,并说“复古”是未来10年的主旋律,提出“星平兰台共参”和“八字多主论”,自认为完成了万民英未能完成的任务(就这么自信!),“填补了五百年来三命术实践运用空白”,已成“近百年来命理学术水平的最高代表”。看过金庸武侠小说的人,相信对这种目空一切的自嗨场面并不陌生。但那些自封的诸多尊号含金量到底如何呢?像万民英那样的大家都未能完成的任务,你就敢说完成了?再说,五百年来名家辈出,像沈孝瞻、陈素庵这些人物都是进士出生,学富五车,尤其是陈素庵身为弘文院大学士,且不说学养和能力,就他所能见到的命理古籍恐怕也是今人难以企及的吧?这五百年来就你看过《三命通会》?就你知道万公提出的设想?
本人素有精神洁癖,本不愿搭理这些呓语,但良知又非逼着我说几句不可。
(一)“复古”与“研古”的区别
最近,我翻看了一些关于“复古”的文章,发现有一个通病:作者从不谈“复古”的概念。什么叫“古”,什么叫“复古”,都没有明确的界定。个人觉得,概念的界定是任何讨论的基石,否则就会出现论战双方自说自话的场面,闹出鸡同鸭讲的笑话来。
通常意义上讲,“复古”指的就是复其旧貌,基本要求就是不走样不变形,更不能是挂羊头卖狗肉。有人说:我们说的“复古”就是指“复”到“三命术”。那好,什么叫“三命术”?“复古”派可能会说“三命术”就是李虚中创立的“三命术”。再追问李虚中创立的“三命术”是什么?他们就不知道了——因为他们从来没给出过答案。陆致极先生倒是从《李虚中命书》中复原了“三命术”的论命框架和方法,但他们又不认可。更逆天的是,居然有人连先师李虚中也不放在眼里,甚至剥夺了他的创始权!有人在自著中声称,“若上不精通五星法,下不精通子平法,是不太可能全盘掌握李虚中三命法的”。照他这么讲,李虚中显然也不掌握李虚中三命法——因为李虚中的时代压根就没有子平法,他哪精通去?
更深一层讲,这里还涉及到“三命术”与“子平术”的关系问题。陆致极先生早就说过,“子平术”脱胎于“三命术”,是对“三命术”的继承与扬弃。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:其一,“三命术”以年为主,采用的是年(含禄、命、身三元)加“胎、月、日、时”(四柱)的论命架构;“子平术”以日为主,采用的是“年、月、日、时”四柱。其二,“三命术”以纳音为主要论命工具,虽不排斥河洛五行,但主要用纳音生克;“子平术”舍纳音而专用河洛五行。其三,“三命术”主要以干支的特殊组合定格局,并以此断人祸福;“子平术”则通过十神之间的生克关系推算其成败寿夭。总的来看,“子平术”继承了“三命术”中的精华,比如五行生克制化、部分十神内容(“三命术”有类似的表述)、旺衰等等,都来自“三命术”。
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?那就是“研古而不复古”。用实证的方法,通过统计和大数据手段,找出古法中可以证实的理论和方法,而不是做全盘接受的“复古”。
(二)“合参”与“复古”不能同时成立
“合参”可以说是“复古”派最具诱惑力的话术。咋一听,不就是用各种方法都算一遍,然后综合参考而用之嘛。但他们所说的“合参”并不是这个意思,而是将本不属于同一个体系的指标和方法东拼西凑放在一起。这样的“合参”是大有问题的。而且“合参”这个词恰巧暴露了“复古”派的软肋。因为“合参”与“复古”在逻辑上恰好是不能同时成立的。
前面已经讲过,“复古”乃复其旧貌,而且不能走样(这其实是做不到的,前面已经论述过了)。为了论证方便,我们姑且认为能够不走样地“复古”,将“五星术”、“三命术”和“演禽”都一一“复活”。那好,这些“古法”是不是都有其独立的系统和方法?如果承认这一点,那你告诉我,怎么“合参”?退一万步说,你将A系统的元素用在B系统上,而且也恰好成功了。那你“复”的什么“古”?记住,“复古”是有其标准的,决不是随意的胡乱嫁接。
如果听不懂“合参”与“复古”在逻辑上不能同时成立的道理,那好,咱们专门来讨论“合参”的可能性。
我们拿二进制和十进制来举例,二者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算法,你怎么“合参”呢?为了说明“合参”的不可能,我们再用“五星术”和“子平术”来说明。众所周知,子平术以四柱干支为基,五星术则以黄道坐标立论,二者在宋代已分道扬镳。为什么现在极少有用“五星术”的?因为它往往需要复杂的天文观测和计算,历史上屡屡因为观测技术的局限和岁差处理等原因出现错误,最终在明末清初被官方判了“死刑”。现在除了国家天文台,试问有谁知道五星在某时某刻的准确坐标?又如何转换为可以通约的运算单位?这些即使做到了,由于运算单位的不同,你又怎么“合参”呢?
(三)“多主论”的逻辑错误
这个问题其实不需要过多的解释。谁见过“多个”天下第一呢?如果有人忽悠你,说你和张三、李四、王二麻子都是第一,你能相信吗?“多主”从逻辑上讲就是“无主”。这么明显的错误,居然还有人信。比如,有人将李虚中讲的干禄、支命、纳音身(以年为主)改为“禄主、命主、身主”,说这就是“多主”,并强调这是他的重大“创新”。可同是这个人,又在别的地方将“多主”定义为同时“以年为主”和“以日为主”,活生生捏造了一条两头蛇。不但全然不顾逻辑能否自洽,而且前后前后表述自相矛盾。与其说叫“多主”,倒不如说是“多变”。
(四)《三命通会》:“三命术”的圣经?
《三命通会》系统收录了李虚中、徐子平等古法和今法的命学理论,保存了《玉井奥诀》《明通赋》等佚文,对命理文献的保存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它对纳音五行的阐释延续了早期禄命法的宇宙观,又引进了 “胎元”“命宫” 等来自唐代星命学的概念。因此,它被《四库全书》誉为 “自明以来二百余年,谈星命者皆以此本为总汇”,堪称命理学的集大成之作。从内容上看,“古法”和“今法”的篇幅差不多各占半壁江山。前面提到,万民英确曾有个古今融合的想法。但他本人并未提出二者结合的论命体系和具体分析方法。
此外,自从《五行精纪》从韩国回流重刊之后,人们发现《三命通会》中有不少段落几乎与《五行精纪》一字不差,而且《五行精纪》里面保存的“古法”内容明显多于《三命通会》,所引的文献种类也较《三命通会》更为丰富。因此,过度神化《三命通会》并将其奉为“古法”圣经,可能是因为对《五行精纪》缺乏了解。当然,还有一种猜测:硬要圣化《三命通会》的目的,可能是想拿万民英讲故事,引出万公未完成的“事业”竟被我完成了的噱头,成就某些人“五百年来第一人”的地位。但愿这纯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。
(五)《兰台妙选》的局限
除了《三命通会》,还有人将《兰台妙选》也视为“古法”圣经,并搬出万民英作注这件事为其张目。《兰台妙选》是重视“象”及干支特殊组合的一种命学理论。但严格来讲,除了都采用纳音论命之外,它与“三命术”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,里面所举例子大都是年月日时四柱,只有少数涉及到胎元。所以,将其奉为圣经,显然过头了。
其实,万民英与今之无条件吹捧《兰台妙选》者是有本质区别的。他在《兰台妙选评注》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:
虽然格局之说架空悬虚,包括广远,中间不论财官之有无,不论主本之强弱,不论岁运之向背,只以某干支见某干支,某花甲遇某花甲,某象数合某象数,或者不能无失。故子平之法徐居易尤得其实也。
这说明万民英先生对仅凭大“格局”论命还是十分谨慎的,并非像那些倡导“复古”的“大师”们讲的那样。这段话,也充分暴露了《兰台妙选》的弱点。翻译过来就是,如果不去看命局中有没有财官等十神,不去分析本主(指年和日)的强弱旺衰,不去看岁运是否与原局配合,只凭干支之间的关系,用“象”和“数”合成的格局去断命,就难免失准。言外之意,光靠这些所谓的“格局”是不行的,还是得用子平之法来分析。
因此,《兰台妙选》尽管在看“贵”命的时候或许有些参考价值,但真正要完整的分析命局,还是没有子平法可靠。
陆致极先生著书与讲学,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,继承和发扬以“今法”为主的论命范式,同时广泛借鉴已经验证过的经验和理法。其实,就中国命理学而言,如果不是打着“复古”旗号故弄玄虚,提倡研古何尝又不是一件大好事呢?但是,怕就怕一些别有用心之人,压根就没深入研究过“古法”,甚至连书都没看过几本(他们的口号是反对“书房派”)就拿此蒙事儿。
如果你有幸看到本文,往后有谁再跟你谈什么“复古”与“合参”,可能就要留个心眼了。
多说无益,就此打住!
附:
简介:
陆致极,1949年生于上海,美国伊利诺大学语言学系博士。计算语言学家、当代著名命理文化研究学者、“时空基因”计量研究的开创者。
早年从事语言学教学和研究,出版有《计算语言学导论》、《计算语言学》、《汉语方言数量研究探索》等专著。
自2006年后,专注于传统命理学研究,取得了丰硕的成果:
一、命理学史研究:著有《中国命理学史论》(2008年),此书是第一本命理文化通史性著作,具有里程碑的意义,有韩文译本;《命运的求索》以及《古法论命纲要》。
二、命理体系和教材:《八字命理学基础教程》、《进阶教程》和《动态分析教程》;《现代八字命理学纲要》、《命学撷英:陆致极八字理论集》以及《细理干支:六十日柱新探》;还有《八字与中国智慧》。
三、出生时间与健康、疾病的专题研究:《又一种“基因”的探索》、《解读时空基因密码:轻松知道你的先天体质》和《疾病早知道:再探时空基因密码》。主张在传承的基础上,应用大数据和现代数理统计工具,拓展研究领域,实现命理学的学术化、现代化。